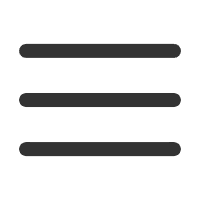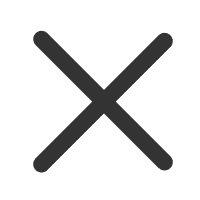原標(biāo)題:春天捎來(lái)時(shí)令滋味(半日閑譚)
四季有“時(shí)令”。
時(shí)令,其實(shí)是個(gè)古詞。“天子乃與卿大夫飭國(guó)典,論時(shí)令,以待來(lái)歲之宜”,所謂“時(shí)令”,原本是依季節(jié)氣候制定的有關(guān)農(nóng)事的政令。所以,“時(shí)令”是農(nóng)耕為主的時(shí)代留給我們的印記。但歷史與時(shí)間早把這種印記轉(zhuǎn)化為我們的生活方式、我們與自然相處的節(jié)奏。
到今天,“時(shí)令”的本義已經(jīng)隱退,但它所引申出的時(shí)間與自然觀念,已成為我們文明傳統(tǒng)的一部分。如今,生活在其中,“時(shí)令”這個(gè)詞最常和食物、蔬菜、水果等搭檔使用。春天的“時(shí)令”是什么呢?我想,有幾種滋味是最值得品味的。
首推筍。
很多人把明末清初的文學(xué)家李漁也視作歷史中排得上號(hào)的美食家。他是這么說(shuō)筍的:“此蔬食中第一品也,肥羊嫩豕何足比肩!”我猜他說(shuō)的是春筍。春季是筍生長(zhǎng)最蓬勃的時(shí)候。季節(jié)來(lái)時(shí),地下的竹鞭上的芽,在等著一場(chǎng)場(chǎng)春雨,長(zhǎng)出地面,就成了春筍。竹子,雖然高大堅(jiān)硬,但其實(shí)是種草本植物。吃竹筍,吃的是它在春雨、春陽(yáng)里與泥土糾纏的一點(diǎn)點(diǎn)時(shí)間。時(shí)令的滋味在取其嫩其鮮。待時(shí)間稍過(guò),就變老變柴,成了竹,和夾筍的筷子近乎是一回事了。
“雨后春筍”,說(shuō)的是它長(zhǎng)得快,也是暗示它最鮮嫩脆的時(shí)間是短暫的。李漁在《閑情偶寄》里也暗示了這種短暫,暗示了筍與地氣的密切關(guān)系:“他種蔬食,不論城市山林,凡宅旁有圃者,旋摘旋烹,亦能時(shí)有其樂(lè)。至于筍之一物,則斷斷宜在山林,城市所產(chǎn)者任爾芳鮮,終是筍之剩義。但將筍肉齊烹,合盛一簋,人止食筍而遺肉,則肉為魚(yú)而筍為熊掌可知矣。”
人氣最足的,卻可能是春餅。
說(shuō)春餅,其實(shí)餅不是重點(diǎn),春才是。正經(jīng)說(shuō)來(lái),它應(yīng)該是儀式感最強(qiáng)的食物之一。群集了春天的菜蔬,包在一張薄薄的面餅之中,卷成一道春天的風(fēng)味。吃下它,仿佛就和春天、和生機(jī)發(fā)生了直接的聯(lián)系。“春日春盤細(xì)生菜,忽憶兩京梅發(fā)時(shí)。盤出高門行白玉,菜傳纖手送青絲。”杜甫記下了唐人借此和春光發(fā)生的聯(lián)系。時(shí)間、食物和風(fēng)俗,在這個(gè)事物上,融為一體。
對(duì)春餅的描述,寫(xiě)活了許多家常食物的作家汪曾祺在《四時(shí)佳饌》里寫(xiě)得最清晰:“立春日吃春餅。羊角蔥(生吃)、青韭或蓋韭(爆炒)、綠豆芽、水蘿卜、醬肉、醬雞、醬鴨皆切絲,炒雞蛋,少加甜面醬,以荷葉薄餅卷食。諸物皆存本味,不相混淆,極香美,謂之‘五辛盤’。蘿卜絲不可少。立春食蘿卜,謂之‘咬春’,春而可咬,頗有詩(shī)意。餅吃得差不多飽了,喝一碗棒渣粥或小米粥,謂之‘溜縫’,如砌墻灌漿也。”“五辛”的寓意,“咬春”之說(shuō)的詩(shī)意,“溜縫”的俗世氣息,都在其中了。
說(shuō)到了春餅,就不能不提提春卷了。
春卷與春餅有相似處。不過(guò)顯然,春卷比春餅更直白一些。“卷”字直陳它的一部分形態(tài),另一部分形態(tài),則交給了它最常搭配的那個(gè)字,“炸”(zhá)——炸春卷。
據(jù)說(shuō)宋末的類書(shū)《歲時(shí)廣記》有記載,“京師富貴人家造面蠶,以肉或素做餡……名曰探官蠶。又因立春日做此,故又稱探春蠶”。蠶字音諧轉(zhuǎn)化為卷,即現(xiàn)在的“春卷”。兩宋都城在北在南,從汴梁到臨安,或許風(fēng)俗由此廣布。當(dāng)然,對(duì)這個(gè)說(shuō)法并不是沒(méi)有爭(zhēng)議的。但無(wú)論記載及流變可信與否,有一點(diǎn)是可以確信的:在南北東西飲食習(xí)慣的爭(zhēng)論中,炸春卷,是難得的那種地不分南北的滋味。春天的菜香和油香,似乎都在這脆脆的一口中。作家崔岱遠(yuǎn)在《京味兒食足》中寫(xiě)到過(guò)這一口:“那時(shí)候的早點(diǎn),常吃他家的炸春卷,酥脆的春卷皮裹著松軟滑嫩的餡料,咬上一口,一不留神鮮美的湯汁就會(huì)淌到身上。”盡管只是文字,卻讓人生出了如在口中的滋味。
不能忘的時(shí)令滋味,還有豆腐。
豆腐,其實(shí)是種四季食物。不過(guò),春日里飲食宜清淡,豆腐就是絕佳的選擇了。而能與它搭配的菜蔬,也以春天里最豐沛。我至今猶能記得老家的豆腐師傅挑著擔(dān)子走街串巷吆喝。等招呼他到門前,看他放下?lián)樱瞄_(kāi)紗布,那豆腐還是溫?zé)帷㈩澪∥〉摹D枚垢肚谐蓹M平豎直一塊塊放到碗里——就是春天的佳肴了。
據(jù)說(shuō)豆腐由劉邦之孫、《淮南子》編者劉安發(fā)明。食物發(fā)明的傳說(shuō)未必確鑿,但水嫩的豆腐進(jìn)入中國(guó)人的食譜,確實(shí)是歷史悠久了。而它也實(shí)在是種宜于日常的食物。所以《城南舊事》的作者林海音說(shuō),“有中國(guó)人的地方就有豆腐”:“豆腐可和各種鮮艷的顏色、奇異的香味相配合,能使櫻桃更紅,木耳更黑,菠菜更綠。它和火腿、鰣魚(yú)、竹筍、蘑菇、牛尾、羊雜、雞血、豬腦等沒(méi)有不結(jié)緣的。”我倒更喜歡她對(duì)豆腐的另一句描述:“它像孫大圣,七十二變,卻傲然保持著本體。”這哪里只是在說(shuō)一種食物的滋味呢?
是啊,時(shí)令滋味又哪里只是食物的味道呢?當(dāng)人們和著季節(jié)的腳步聲,背著家鄉(xiāng)滋味翻山越嶺甚至遠(yuǎn)渡重洋的時(shí)候,它的意味才最是深長(zhǎng)。(吳畫(huà)成)